叶兆言很喜欢肖全给自己拍的一张照片:在一堵光秃秃的墙前,他穿着白色背心,眉头紧锁。那是1991年8月的一天,他带着肖全去食堂吃饭,午后阳光正好,便在院子里留影。他记得院子里有一棵泡桐,一到冬天就会挡住阳光,他总要在某个日子,拿起菜刀,嚓嚓嚓地砍树。
当时叶兆言刚买了一台电脑——此前他用的是四通打字机,每天拼命打字写作,“有时做梦也在写,所以总是一副疲惫的样子”。直到现在,他仍时刻保持一种写作的状态,即便是接受采访,身边的电脑也是开着的。他自嘲是“一个热爱写作的老家伙”——每天像工人做工一样考勤打卡,天色刚亮就坐到书房里,打开电脑,写作或者冥想.一待就是六七个小时,“一直到写不下去才停”。
这一写作习惯是祖辈留下来的。每当忆及祖父叶圣陶,他的脑海里都会出现一个画面:80岁的祖父伏在案头,有时写信有时读书,一坐就是8个小时,天天如此。30多年过去,祖父的背影一直定格在他的脑海中,挥之不去。
“这让我明白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:作为一个作家。你是要工作的。你的姿态就应该是一个人坐在那儿,给别人一个背影。”叶兆言说。就在这日日伏案写作的背影中,他的书一本一本地出,最新推出的小说便是《刻骨铭心》。
民国儿女们的爱与痛
《刻骨铭心》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,军阀混战,日军侵华,南京这座城处于风口浪尖之上。城中的青年男女绍彭、丽君、希俨、秀兰等。在动乱中命运悲欢交织,有人成长为真正的革命者,有人从富贵跌落,在凄惨中结束生命。
“我的脑子里总是有很多东西,虚构的、非虚构的;历史的、现实的。有一天看到‘刻骨铭心’四个字,好像找到了一根绳子,把头脑中零散的东西串起来。”叶兆言对《环球人物》记者说,这个故事早就有了,只是一直没有写。
叶兆言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,关于南京的书写,他早已轻车熟路。无论小說,还是散文,他一直游荡在这个城市的历史与现实之间,有时写市井小人物的悲欢离合,有时写大历史的巨变沧桑。这次写《刻骨铭心》,他也将一些南京史实穿插在虚构的故事中间。
主人公绍彭一出场,便在秦淮河边的桃叶渡,拿着大蒲扇给国学大师章太炎扇风,后者正给一众年轻人讲典故。随后高云岭45号、雨花台、乌龙潭等南京真实地名一一出现,亲身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美国传教士魏特琳也现身其中一章……“感觉不时被点到穴位。”同样生活在南京的作家鲁敏说,她觉得这是一部“最南京”的小说。
但在叶兆言本人看来,这些真实的历史只是“一种技术活”,“就像空的房间挂上一幅画,只是点缀。主要是为了吸引读者,让他们走进去,看下去。小说不以历史、掌故取胜,最重要还是它所要表达的内容,它是否能打动人”。
写《刻骨铭心》时,他常常会想到张爱玲的《金锁记》。那是一个压抑的故事:年轻的曹七巧嫁给大户人家的残疾儿子,欲爱而不能爱。在财欲和情欲的压迫下,她变得扭曲、乖戾。丈夫死后,她为控制女儿。让她养成很多坏习惯,包括抽大烟。后来,女儿遇到心仪的男人,悄悄戒掉大烟,而当男人来求婚时,她说女儿“抽完大烟就下来”。
“为什么一个做母亲的人,要处心积虑地毁掉女儿的幸福?”叶兆言自问,顷刻间又给出答案:“这就是张爱玲的过人之处,她看到了人性中那种无奈的痛。这种痛很揪心,让人忍不住要叹息,忍不住要呐喊。”以此为参照,他写民国时代南京儿女们的爱与痛。
小说后半段,丽君的第二任丈夫冯焕庭,曾是一手遮天的军阀。日军屠城,军队抵挡不过,他不得不躲在自家阁楼上。一日,眼看自己和前妻所生的女儿锦绣即将被日军侵害,他选择站出来,最终被日军杀害。之后,丽君和锦绣没了靠山,人生也一点点滑落——一个在穷困和疾病中死去,一个嫁给年长自己许多的剧作家。
写完后,叶兆言拿给女儿看,女儿边看边哭,“后来我告诉她。写这一段时我也是哭的”。
“文学就是这样那样的一些痛,而痛中间始终有善。事实上,有了善才能更确切地感受到痛。痛的底子,加上善,才会更刻骨铭心。”叶兆言说。
俗与不俗,是写作的重要标准
每每提及叶兆言,难以回避的是他的家世。
祖父是著名文学家、教育家叶圣陶,父亲叶至诚也是作家,曾任文学期刊《雨花》主编。但无论是祖父还是父亲,都不曾有意识地培养他成为作家。父亲被打为右派后,一度对文学充满了恐惧,于是从小就教育他:长大后干什么都可以。但是只有一条,不要写小说。
“后来之所以成为作家,与我少时的阅读有关。”叶兆言说。
祖父曾留给父亲一个高大的书橱,把一面墙堵得严严实实。这面由书砌成的墙,成了叶兆言童年时代最先面对的世界。为了教他识字,父亲做了很多卡片,上面写上端端正正的方块字。父亲忙于工作时,他就拿着卡片,踮起脚站在书橱前,对着书脊找自己认识的字。9岁那年,因为“文革”,家中的书籍都被没收,“看着父亲借了一辆手推车,将家中的藏书送往指定地点,一趟又一趟”。
3年后,收缴藏书的房间要腾出来给一对年轻人做婚房,那些书有幸被归还。叶兆言又开始了天天与书相伴的日子,“无聊于是读书,孤独然后看小说”。譬如爱伦堡的《解冻》、萨特的《厌恶及其他》、加缪的《局外人》等,都是那一时期读的,“影响最大的一套书是爱伦堡的《人·岁月·生活》,厚厚六大本,它们断断续续地提到一大堆当代作家,对我来说都是活生生可以效仿的对象”。
因为父亲的教导,叶兆言从小就没想过当作家。他喜欢玩半导体无线电,后来还迷上照相机。1974年初夏,叶兆言到北京照顾叶圣陶,为爷爷当了一年“秘书”,和他聊天,陪他和朋友见面,在他身边乱看书。“爷爷说《战争与和平》好,我就读《战争与和平》。他说巴尔扎克好,我就读巴尔扎克。这样的阅读,有一个好处,让我武装到了嘴皮子,可以到处卖弄。”
有一次,他看到爷爷的案头上堆着一摞厚厚的小说手稿《李自成》——当时很多作者将作品送过来,指望叶圣陶在语文上把把关,他拿起就读,“一口气读完后,爷爷问我感觉怎么样,我也说不出好坏,只知道故事挺好看”。8年后,由姚雪垠所著的《李自成》(第二部)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。
也正是在那段时间,叶兆言深受堂兄三午的影响。“谈起文学的启蒙,三午对我的影响耍远大于父亲,更大于我祖父。”三午是一位诗人,和北岛、芒克、多多等都是朋友,这些人后来都在诗坛名震一时。
有一阵子,叶兆言整天缠着三午给他讲大仲马的《基督山伯爵》。三午很会讲故事,每每讲到关键时刻就突然停下,然后让他买烟,为此花了他不少零用钱。“但这种卖关子说故事的方法显然影响了我,告诉我应该如何去寻找故事,如何描述故事,如何引诱人,如何克制,如何让人上当。”
在三午的影响下,他很早就知道并熟悉那批朦胧派诗人,读过、抄过他们的诗,甚至有过一个短暂的文学理想——成为一名像多多那样的诗人。他至今仍记得三午拿着多多的诗,大声地朗读,然后大喊一声:“好,这一句,真他妈的不俗!”
“当年那些让我入迷的先锋诗歌,奇特的句式,惊世骇俗的字眼,都成为我文学的底牌,也是我最原始的文学准备,是未来的我能够得以萌芽和成长的养料。”叶兆言说,从最初接触文学开始,他的文学观就是反潮流的,“要持之以恒地和潮流对着干,要拼命地做到不一样,要‘不俗’。”
俗与不俗,后来成为叶兆言写作时的重要标准,一直到现在。
从北京回到南京后,叶兆言进入工厂做钳工。1977年,国家恢复高考,他便自学高等数学、微积分,准备考医学院。但因为眼睛受过伤,体检不合格,只能选文科。第二年,他收到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,父亲没有一句祝贺,只是感叹了一声:“没办法,又耍弄文了。”
写什么都被发表,对作家也是一种伤害
《刻骨铭心》的最后一章,名为“有点多余的匆匆结尾”。叶兆言在其中提到了自己的长篇小说《没有玻璃的花房》,在这一作品中,他写到过一个叫李道始的人——戏剧学校副校长,也是《刻骨铭心》中锦绣夫妇所在的学校领导。
“一个作家的写作是连续的。其实我还有一点小私心,想让读者去看我之前的作品。我从不过高估计自己,每一次写作都很用力,都把它当作对以往作品的拯救。”叶兆言说,在写作这件事上,他从来不是一个信心十足的人——即使到了现在,还是不太相信读者已真正接受了自己。
上世纪70年代末,叶兆言开始偷偷摸摸地学写小说,因为“不相信自己能写好”。他曾写过短篇《白马湖静静地流》,寄给北岛,想试试看能否在文学杂志《今天》上发表。北岛给他回了信,说小说写得不好,建议他可以尝试多写一些诗歌。
他没有听从这一忠告,仍断断续续地写小说,偶尔也有发表。但基本上没有任何反响。“大部分寄出去的小说,最后像放飞的鸽子一样,一只接一只地又飞了回来。”到了80年代末,他的中篇小说《枣树的故事》和《夜泊秦淮》发表,引起文坛轰动,人们这才知道了叶兆言。
《夜泊秦准》是叶兆言写作生涯上的转折点,“好像我面前有一堵墙,突然开了一扇窗户,我从窗口可以看到无限的风景”。这部作品讲述从清末到上世纪40年代,南京城里小户人家的悲喜传奇,士绅门第里的情欲角逐,将军阀旧妓、腐儒名士、贵妇名媛诸色人等写得活灵活现。“戏仿民国春色,重现鸳蝴风月。”著名学者王德威曾如是评价。
那个年代,正是文学最为风光的年代,小说家、诗人都是青年人追捧的偶像。同一时期,马原、余华、苏童、格非等青年作家纷纷登上文坛,叶兆言和他们一起被冠上“先锋作家”的称号。
“我希望自己千万不要被某一种理论预设限定,尽量不要作为某一个流行派别中的一员。”回望80年代,叶兆言有诸多感慨——毕竟那里有一代人最好的青春年华,但也并不留恋,“先锋成名之日,就是先锋消亡之时。但先锋的姿态要一直在。真正的好作家永远都应该是革命者。”
之后的每一次写作,叶兆言都试图与之前不同。他在《花影》《花煞》中写怀旧神话,在《古老话题》中讲犯罪故事,《没有玻璃的花房》则是成长小说。到了《刻骨铭心》,他选择在结构上另辟蹊径,写了一个与小说无关的“冗长”的开头,讲述了两个现代故事——一个与无性之痛有关,一个与失去语言之痛有关,但都刻骨铭心。
“写作必须要冒险。”叶兆言说,他记起小时候看露天电影,草地上扯一塊大白布,天一黑人们都聚集在幕前,盯着那块白布张望。他则常常跑到银幕之后,默默地研究倒影,“生活和写作也一样,总需要我们换个角度重新思考”。
就这样,他时刻保持着警觉和清醒,“永远写作在文学圈之外”。“因为文坛是世故的,它把所有的成功写作者都纳入自己的范围。但写什么都被发表和承认,其实对作家也是一种伤害。”
这段日子,叶兆言正在为非虚构作品《南京传》收尾。他从三国写起,写重大历史关头南京城里的人和故事。起初他拒绝写,因为想要回避南京。琢磨许久,他找到一个新的角度,便有了野心——通过南京这扇窗户来写中国的历史。
生于南京,长于南京,他并不喜欢将自己和南京绑在一起,但也在写作中认清了现实。“作家写作、从事文学活动,脚下必须要有一块坚实的土地。南京就是我的土地。”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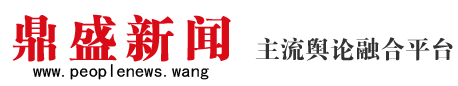


 010-65360000
010-65360000 23038485@qq.com
23038485@qq.com
